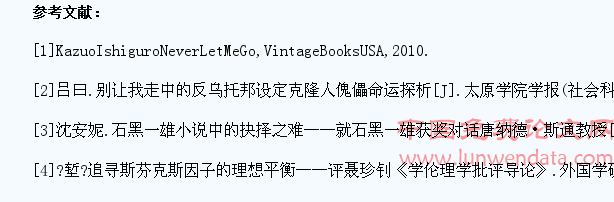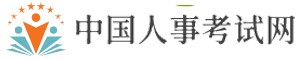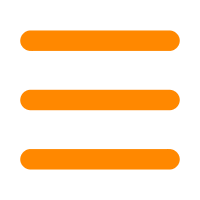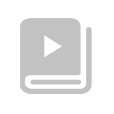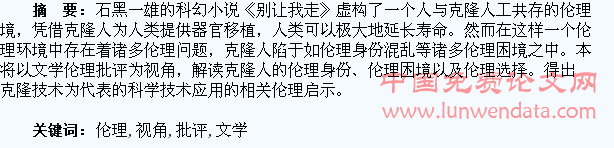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写于2005年的科幻小说《不要让我走》的为读者虚构了一个人类和克隆人并存的伦理环境。书中克隆人卡西作为第一叙述者,回忆了自己应召成为器官捐献者之前和好友鲁思、汤米在克隆人学校海尔森学习,毕业后在农庄生活和看护捐献者的岁月。作为为患患者类提供脏器而被培育出来的克隆人,卡西与她的同伴们自出生以来就和普通人类过着截然不需要的生活,甚至从肯定的程度上来讲,克隆人的生命价值在于被剥夺。器官“捐献者”克隆人面临着多重伦理问题:对自己存在的质疑,生活目的的缺失,对很难完成多次捐献的“使命”的担心与不可以延缓捐献而获得多一些时间伴随爱人的愁苦。聂珍钊教授觉得: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只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特征与作家创作的伦理学问题,而且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关系的种种现象,这其中包含文学怎么样在虚拟的世界里再现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伦理现象。文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伦理学的批判对象,主要在于文学借助我们的特殊功能吧人类社会虚拟化,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几乎有了伦理学所要研究的全部内容①P10。本文意欲从文学伦理批评视角解析作品《不要让我走》中的克隆人的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伦理困境(ethical prepcaments)、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s)与从克隆人无私捐献器官的行为中研究其所带来的伦理启示。
1 克隆人的伦理身份
聂珍钊教授觉得: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寻在的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决定血亲人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得的,如老公和老婆的身份①P263。
克隆人童年在克隆人学校海尔森度过的,学校位居平坦低地,周围土地高起,与世隔绝。克隆大家没办法通过和社会上普通人进行对比和他们的评价来获得我们的身份信息,不可以进行身份认知。卡西和其他同伴们都被叫做“学生”,他们既无爸爸妈妈兄弟也没一个完整的名字,如卡西·H、汤米·D。克隆人只不过拥有科技的人类生产出的一种“器官商品”,并非人类爱情的结晶。克隆人没家族历史,整个人类通过生物进化的完成的自然选择,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文明进步也与他们无关,克隆人从来不会由于自己是“人”,智商水平高于其他物种而产生出一丝骄傲。他们在校期间能接触到的普通人类只有管理学生学习生活的“监护人”。学校方面一直向学生们强调他们是“特别的”,却极力回避对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做出说明。卡西时常对监护人的需要感到模棱两可,她思索着自己的特殊性,不知道为什么采集画作的夫人将他们视为“蜘蛛”般躲避着,更不知何故夫人在撞见自己和着歌曲Never let me go起舞时而流泪。好友汤米烦恼于露西小姐为什么要在告诉他创造力无关紧要之后又骤然改变立场。学生们不解于露西老师为什么断然否定他们对将来的职业畅想。一次一次突兀又模糊的对学生们探索自我身份的思想否定与行为的不支持,使得卡西他们没办法打造身份认知。
毕业后,卡西和和同伴们搬入农庄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克隆人共住。与在校的懵懂期不同,学生们也日渐知道了我们的“特别”和“器官捐献”的实质。离开学校的他们仍以学姐学长相称,内心深处仍觉得自己是“学生”,即便社会未给出“学生”明确的身份概念。克隆人极为重视他们的生命来源,虽没办法逃脱捐献器官的悲惨命,他们依然对生命可能性怀有期望。鲁思曾借助外出机会探寻过她的根源,因发现自己风韵举止与他们相差甚远而大失所望。她说道:“大家心里了解得非常,大家都是拿那些毒虫、妓女、酒鬼、流浪汉之类的人渣作为模型制造出来的。可能还有囚犯,只须不是精神病患就没问题,那才是大家的生命起源。”
全书从未提及克隆人和人类的根本性不同。卡西、鲁思和汤米间的友谊与人类无异。克隆人有同情、愤怒、悲伤、失望、爱,有着人类拥有些所有情绪,他们一样有创造力,有灵魂。反而是人类以克隆人没灵魂为托词拒绝承认克隆人是具备社会意义的“人”。社会用冷漠对克隆人筑起高墙,他们切断了和克隆人的所有联系,仅仅在需要延长寿命之时,提取器官。索取却不知感谢,况且这种索取还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克隆人的伦理困境
在文学伦理批评学中,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因为伦理混乱(ethical confusion)而给人物带来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冲突。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致使的困境①P258。克隆人面临多重伦理困境。克隆人的既无明确的伦理身份也无人权,即便没触犯法律,人身自由也要遭到严格限制。卡西他们需要一直签到,即使汤米在完成第三次捐献后依然不可以被免除此程序。在人类眼中,克隆人是“仓库里的货物”,不可以丢失。克隆人只有两种选择,服从人类安排或者反抗人类,这便形成了书中最大的伦理悖论(ethical paradox)。假如卡西他们根据人类的安排,捐献器官直到死亡,他们就会失去感受世界、感受生活的美的的权利与追求梦想的机会,失去为 “人”存在的意义;假如克隆人反抗人类,或许会致使人类愈加无情的攫取器官——在克隆人自我意识尚未打造、完全蒙蔽的状况下剥夺他们的生命。同意捐献命的克隆人视捐献次数为他们的唯一荣耀,由于他们想通过尽可能放大自己生命的价值的方法,获得人类尊重。然而,捐献—恢复—再捐献的过程使克隆人的身心备受煎熬。“大家一直听到其他人怎么说第四次捐赠之后,嚴格来讲,即使这个生活命已经结束了,但可能还有某种意识存在,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捐赠,数也数不清” ②P348。一次捐献后的成功恢复预示着下一次捐献的痛苦,捐献的终局是死亡。 3 克隆人与的伦理选择
人的生物性选择是人形式的选择,人通过伦理选择才真的的把自己同兽不同开来,伦理选择是人本质的选择。克隆人是人类的科学产物而非自然的产物,他们已经获得了人的形式。同样克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伦理意识这类伦理意识最后帮助克隆人做出了伦理选择。善恶的观念也随着着伦理选择渐渐形成①P266。卡西在从事看护工作的十二年间,她一直忍耐着一次次送别捐献者的伤痛,殚精竭虑周旋于医院和捐献者之间,努力为捐献人提供满足他们需要的服务。卡西未曾由于奔波的劳累,心理的重压而舍弃过看护者的工作。鲁思历程捐献之后幡然醒悟,为当年横刀夺爱伤害卡西的行动深感懊悔,在生命的最后,努力解除去卡西和汤米的误会并提供了申请缓捐的有关信息。汤米更是完成了多次捐献。进行伦理选择之后克隆人也终于获得了他们的伦理身份——捐献者、看护者和“人类”。无论是作为捐献者还是看护人他们都在有限的生命里完成了他们的伦理选择,为了人类献出了他们的所有,用“博爱”的伦理选择延续了人类的生命。即便这种选择充满了悲剧性,但他们都获得了作为“人”的本质。
聂珍钊教授觉得: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合在一块,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人同兽有什么区别,在于人身上的人性因子可以控制兽性因子。克隆人是完整的人,他们有愤怒的冲动,存活的原欲,有掠夺别人幸福的兽性因子,有邪恶的想法;克隆人也有为别人奉献人性因子,他们是有灵魂的。克隆人最后的伦理选择都是“利他”。相比之下,人类已被兽性因子主导,凭着着科学的强大力量,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漠视克隆人的存活权利,甚至借助“克隆人没灵魂”一说自欺。好似埃米莉小姐所说“大家所面对的这个世界需要学生捐赠器官。其次,却又反对把你们当做真的的人类”②P327。人类仿佛变成了丛林之中的猛兽,对所有生灵行驶支配。抢夺克隆人器官人仿佛拿着镰刀的死神收割无辜人的性命,历程了自然选择的大家身上的人性光辉暗然失色。可以想像,没办法做出“善”的伦理选择的人类会遭到惩罚。
4 结语
提及在伦理选择阶段,人类从伦理上把自己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变成了现代的伦理人。科学年代,人类则要历程或者正在历程一个科学选择的阶段,使人变成科学的伦理人①P252。《不要让我走》作为一部预言式小说,对现实是有启发意义的。人类没办法对克隆技术打造起的伦理观念将会致使克隆人和人类的“两败”。试问,倘若人类的生命可以随便延长,生活的失败可以参考爱好随便修改。人类由于生命只有一次,面对绝望的打击可以凭着对生命的珍视,一次次勇敢振作的能力会不会消失;人类寿命的大大延长是不是致使人类不再看重和别人的感情交流,忽略对现实世界美的体验;人与自然、与人之间的异化程度是不是继续加深,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会不会变得脆弱没办法在自然环境中继续存活。全书克隆人未曾对设立器官捐献机制的人类提出一次抱怨,倒是人类自己质问他假如不借助克隆人的器官该如何解决,质问克隆人怎么样构建养育克隆的机制。人类以不愿回到癌症不可治愈的黑暗年代的逻辑给克隆人整个群体带来无尽黑暗,直到最后都没领会克隆人的诉求。小说的题目Never let me go充分体现出克隆大家对自己宿命的无奈对世界的眷恋与对人类人性最后的呼唤和乞求。人类需要紧张起来,在科技改造世界时,明确我们的伦理义务和责任,做出关乎于“善”的伦理选择。